
有人說,“中華民族是一個圓,周長可大可小,圓心無處不在,而半徑就是漢字,漢字就是中華民族的向心力。”每一個中國人都依賴漢字所創造的文化而存在。
電視紀錄片《史說漢字》是國內第一部用電視藝術全景記錄、展示漢字起源及發展歷史的專題紀錄片,是向公眾展示、傳播和弘揚漢字文化的有益嘗試。
該部紀錄片包括《》(已推送)、《》(已推送)、《》(已推送)、《》(已推送)、《》(已推送)、《百年沉浮》、《方正流長》七個部分,以字體的演變貫穿的脈絡,在浩繁的歷史中尋找與文字演變發展有關的事件和人物,用漢字故事講述中國文明的歷史。
【解說詞】

1894年,甲午中日戰爭中,清政府慘敗。消息傳來朝野震驚,京城徹夜時聞哭聲。為什么一度位列亞洲第一世界第七的北洋水師竟被日本海軍打敗?為什么這個兩千年來一直以中國為師的小小島國在經歷了師法西方的“明治維新”后就變得如此囂張?而西方,究竟為什么強大?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王理嘉介紹:有些知識分子覺得洋人之所以能洋槍大炮、國富民強,就是因為他們的文字簡便,認識了幾十個字母就能讀書寫字,所以民智早開。反過來看我們的文字, “天下之至難者”,難寫、難認、難記,所以實現普及教育、救國圖強就是要革漢字的命,要改革漢字。
然而,漢字與中國文化休戚相關,幾千年的積淀使它一脈相傳,改革究竟從何而起?廈門鼓浪嶼,中國第一批通商口岸中的小島,在百余年的漢字沉浮中,它將掀起最初的波濤,而在波濤中最先乘風破浪的,是一個叫盧戇章的人。他懂英文,到過南洋,他想要讓中國富強,要普及教育,必須改革漢字。改成什么樣子呢?就是要像西方的拼音文字那個樣子。他有了這個想法,而且要付諸實踐。1892年,盧戇章編寫的《一目了然初階》出版,這是第一套由中國人創制的漢語拼音方案。由此,漢字改革的大幕以拼音運動的形式正式拉開,并因盧戇章的“切音新字”而命名為“切音字運動”。在《一目了然初階》的封面上,我們看到了這樣一副對聯:“一目了然,男可曉,女可曉,智否賢愚均可曉。十年辛苦,朝于斯,夕于斯,陰晴寒暑悉于斯。”公元1900年,是中國農歷庚子年,這年夏天,爆發了八國聯軍侵入北京的庚子國變。也正是這一年,另一位切音字運動的倡導者以“臺灣和尚”的身份出現在山東沿海的港口,他搭乘的船并不是來自臺灣,而是來自日本,來者也并不是和尚,而是被朝廷通緝的嚴拿罪犯,他的名字叫王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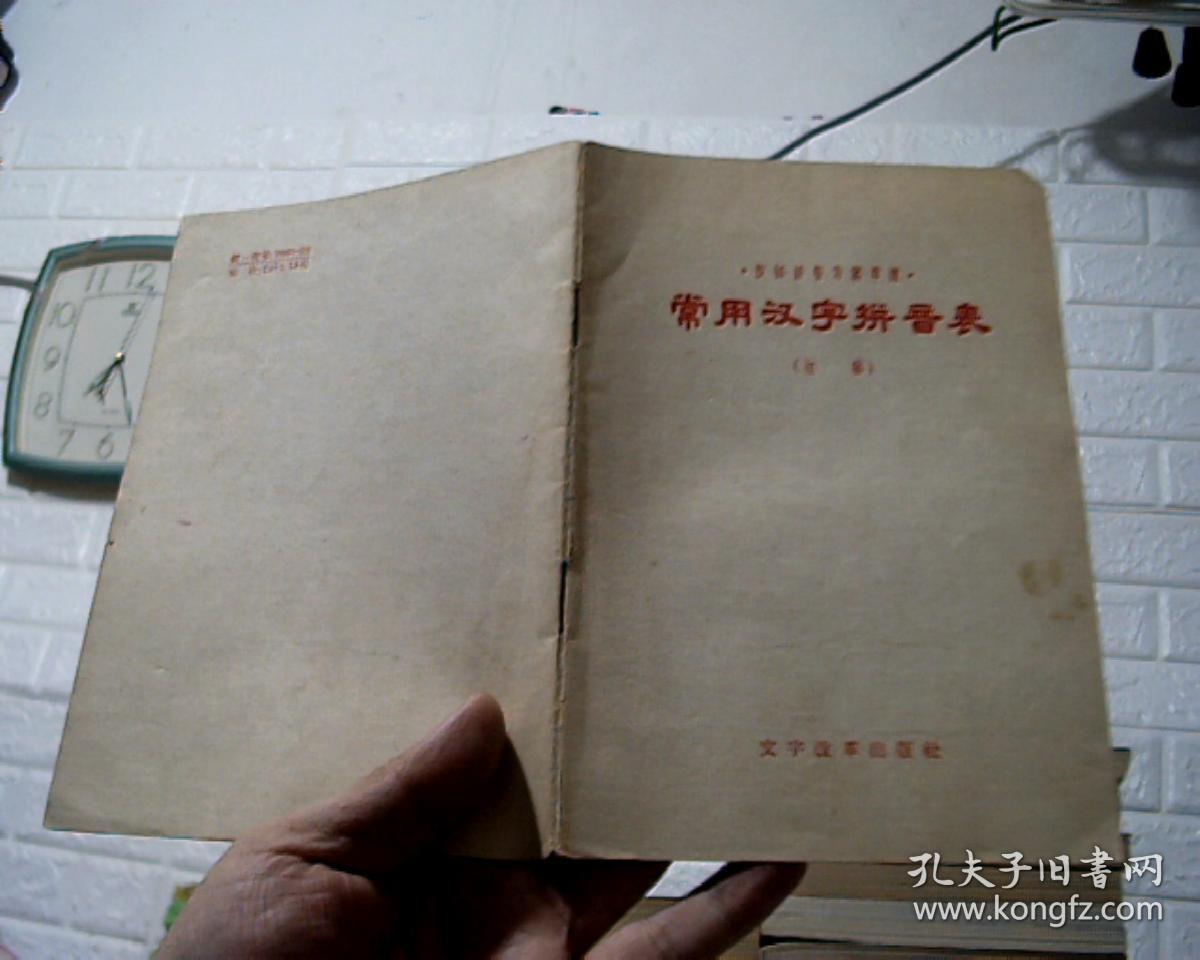
王照曾經是戊戌變法中的風云人物,變法失敗后逃往日本。沒有人能想到信息交換用漢字編碼字符集基本,他此次冒著生命危險秘密回國,是為了推廣一套叫做《官話合聲字母》的拼音方案。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王理嘉介紹:它是第一套漢字筆畫式的拼音方案,是受日文片假名的影響,用的漢字的偏旁來做成一個表音字母,比如說,他取漢字里頭的“撲倒”的“撲”,用一個提手旁的偏旁就來代表我們現在的聲母“p”。 1903年,王照秘密進京,在裱褙胡同創立了“官話字母義塾”。由于身份特殊,他讓學生在前面講授,自己則躲在屏風后面指點。官話字母的影響力正漸漸擴大,這時,王照卻做出了一個出人意料的決定:去自首。這樣在出獄以后,反而可以公開出面推廣《官話合聲字母》。這是冒著生命的危險。經過一番磨礪,王照終于出獄,此時的他更為堅忍執著,全力推行他的拼音方案。幾乎于此同時,盧戇章又編寫了一套新的拼音方案《中國切音新字》,1905年,他專程將此書送到北京,滿腔熱忱地希望得到清政府的支持。然而,方案呈交了三次,全部被駁回。晚年的盧戇章仍在堅持教授切音字,有人贈他這樣一幅對聯“卅年用盡心機,特為同胞開慧眼。
一旦創成字母,愿教吾國進文明。” 據統計,1892到1911年的切音字運動,共提出切音字個人方案28種,掀起了中國漢字改革的第一個高潮。就在切音字運動的實踐者們在外來文化的啟發下以拼音的方式為漢字改革尋找出路的時候,漢字簡化,這條從漢字自身的演變規律中延伸而來的變革之路開始登上歷史舞臺。陸費逵,中華書局的創始人,一位有著革新思想和實業精神的教育家、出版家。1909年,他在主編的《教育雜志》上,率先發表了名為《普通教育應當采用俗體字》的文章,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公開提倡把簡體字作為正體字使用,奏響了中國簡體字運動的前奏。其實信息交換用漢字編碼字符集基本,漢字的簡化由來已久。早在三千年前,神秘的甲骨上就曾出現同一個漢字的簡體和繁體。在兩千多年前的敦煌漢簡,在上面我們也發現了許多形體與今天相同或相似的簡化字。在綿延流長的名家書法中,在不同年代的字書、碑刻中,它們的身影隨處可見。這些在民間“不脛而走”的簡體字通常稱為俗體,與官方正體并行存在。從遠古的刻符到甲骨文、金文,從篆書到隸書、再到楷、行、草,簡化一直是漢字演變的總趨勢。事實上,在晚清,簡體字也曾以正體的身份出現,只是,與它的出現相關聯的是一段驚心動魄的悲壯歷史。1851年1月,洪秀全在廣西金田率眾起義,建號“太平天國”,一場風起云涌的農民戰爭由此拉開序幕。這張已經十分模糊的印刷品,是1852年9月太平軍進攻長沙時東王楊秀清和西王蕭朝貴發布的誥諭。誥諭的內容已很難辨認,但用簡體書寫的“太平天國”卻異常醒目。有趣的是,其中的“國”字比今天還要少一“點”。在太平天國,簡體已成為官方標準用字,政府的錢幣、印璽,爭戰的令旗,印發的布告、書籍等,都采用了唐宋以來在民間流行的以及部分自創的俗體字。雖然太平天國最終失敗,但他們在漢字簡化上的實踐卻給后世留下了很多啟發。

1919年,一份讓中國人蒙受了巨大恥辱的和約,再次將變革與圖強深深烙進國人的心靈。在一戰結束后的巴黎和會上,西方列強公然提出,把戰敗國德國在中國山東的特權,全部轉讓給日本。作為戰勝國參加會議的北洋政府竟然準備簽字接受,這激起了國人的強烈憤慨。5月4日,北京學生舉行了大規模示威游行,一場聲勢浩大的愛國運動迅速蔓延。令人屈辱的現實喚醒了清末以來的沉痛記憶,強烈的愛國使命激起了青年志士對傳統的猛烈攻擊,由陳獨秀、胡適、魯迅等人發起的新文化運動再度高漲,一系列激進的主張紛至沓來,漢字改革首當其沖。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蘇培成介紹:五四時期激進派從挽救中國這個角度出發就提出來“漢字不滅,中國必亡”。他們認為漢字的根本改革就是改用拉丁字母的拼音文字。當然他們對漢字的看法也受到了當時的局限。
此時,“一件驚人的革新事業”也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1922年,錢玄同就在國語統一會里頭明確地提出了一個減省現行漢字筆畫的提案。提案分析了簡體字的構成方法,要求承認簡體字的合法地位。國語統一籌備會通過了這項提案,并由錢玄同、胡適等十五位委員組成漢字省體委員會,一系列提倡簡體字的文章和書籍陸續刊登出版,簡體字運動有了突破性進展。但是,此時的中國,軍閥混戰,漢字改革、教育救國的夢想真的可以實現嗎? 1935年春,一篇名為《推行手頭字緣起》的文章突然在諸多報刊同時出現,文章選定第一批手頭字300個,由蔡元培、邵力子、陶行知、郭沫若、巴金等200名文化界人士和15家雜志社聯名發表。隨著簡體字運動的日益發展,1935年8月,國民政府教育部采用錢玄同主編的《簡體字譜》草稿的一部分,公布了《第一批簡體字表》,共計324字,同年10月,國民政府以中央政府主席、行政院長、教育部長的名義通令全國,要求全國推行。然而,事情很快有了變化。1936年2月,教育部奉行政院命令,訓令“簡體字應暫緩推行”。但是,扎根于群眾的簡體字不推而行,在共產黨領導的地區,簡體字獲得了蓬勃發展。自清末以來,漢字改革的道路漫長而艱辛,但普及教育的目標卻始終不曾獲得真正的成功,漢字改革的方向究竟在哪里呢?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十天后,在毛澤東、劉少奇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直接關懷下,第一個全國性文字改革組織——中國文字改革協會宣告成立。此后,一系列文字改革機構相繼誕生。1952年2月,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成立。1953年10,中央文字問題委員會成立。1954年10,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建立。它們的誕生,拉開了新中國文字改革工作的序幕,也顯示了一個新生國家改革古老漢字的決心和力量。可是,建國初期,百廢待興,文字改革為什么會在新中國的締造者心中占有如此重要的位置呢?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蘇培成介紹:這和新中國剛建立,當時文盲眾多,我們又要進行大規模的建設,必須發展教育,掃除文盲,跟這個背景是密切相關的。毛澤東主席在1951年就明確講過,文字必須改革。開國大典上站在毛澤東和劉少奇中間的老人叫吳玉章,也就是后來的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主任。早在1928年,吳玉章就曾與瞿秋白等人一起探討中國文字改革的途徑和方案,并組織發起了拉丁化新文字運動。但在文改會建立之初,這位元老級的人物卻語重心長地做了一次自我檢討。他說以前是認為文字是有階級性,所以我要把漢字作為一個封建文化來推倒它,這個認識是錯誤的。第二個,我沒有來很好地考慮中國和廣大群眾的習慣和歷史,急于用拼音文字來替代漢字,他說這個也不好。第三個,他說我沒有很好地來研究中國的歷史和現狀,怎么樣能夠讓這項工作符合中國現實的需要。1955年10月,一個在文字改革上舉足輕重的會議召開了,這就是“全國文字改革會議”。在會議開幕的時候,陳毅副總理說了這樣一段話:“在有幾萬萬文盲的國家里,不可能建成社會主義社會,不可能有強大的工業建設。”新中國從現實情況出發,提出了當前文字改革的三項任務,就是簡化漢字、推廣普通話、制訂和推行漢語拼音方案,這樣就形成了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我們整個的文字政策。1956年1月28日,經過語言文字界最頂級專家的整理,在吸納了約20萬語文工作者的意見和建議后,國務院通過了《關于公布〈漢字簡化方案〉的決議》。
《漢字簡化方案》的公布,是對千百年來流行在民間的簡體字的規范,是對清末以來漢字簡化運動的總結,也是新中國文字改革工作的第一項成果。據2004年公布的中國語言文字使用調查數據顯示:截至上世紀末,我國有95.25%的人平時主要寫簡化字。在《漢字簡化方案》制訂和頒布的同時,《漢語拼音方案》的制訂工作也在緊鑼密鼓地進行著。1958年2月11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正式批準通過了《漢語拼音方案》。方案吸收了以往注音系統的優秀成果,采用國際通用的拉丁字母,實行音素化拼音方法,輔助學習漢字。從新中國第一個全國性文字改革組織的籌劃到兩個方案的出臺,吳玉章傾注了大量心血。為了解方案的推行情況,他走遍了大半個中國。簡化字,漢語拼音,普通話,在今天的小學課堂上,這樣的教學內容已司空見慣。
在這個全新的信息網絡時代,通過基礎的識字教育,以普通話的讀音為標準,利用拼音輸入漢字,孩子們可以輕松地遨游網絡,搜索和傳遞信息。半個世紀前的文字改革帶給今天的便利,已遠遠超出當時的想象。但是,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當信息化的浪潮剛剛襲來的時候,古老的漢字面臨的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挑戰:如果漢字不能夠像拼音文字那樣進入電子計算機,中國將被排斥在信息化時代之外。此時,研究漢字的信息處理問題已刻不容緩。幾千年來,漢字的命運從來沒有如此緊迫地與一項技術聯系在一起。1974年8月,周恩來總理親自聽取匯報,研制漢字信息處理系統的工程很快由國家計委批準立項,定名為“七四八工程”,列入國家科學技術發展計劃。1975年,一個長期在家病休的人偶然聽說了這項工程,他抑制不住內心的激動,竟拖著孱弱的身體自發地研究起來。這個人叫王選,當時還只是北京大學無線電系的一名普通助教,但在不久的將來,他將改變一個時代。那時,王選經常是中國科技情報所外文資料的第一個借閱者。經過一番鉆研,他把研究方向鎖定在“七四八工程”中的“漢字精密照排”項目上。20世紀70年代的西方,基于計算機的“電子照排技術”已經大規模使用,而中國仍然處在“鉛與火”的活字印刷時代。但是,要想讓計算機排版,首先要在計算機里存貯漢字信息,而當時的國產計算機內存只有64K。那么,究竟怎樣解決這個巨大的難題呢?數學出身的王選開始沉浸在漢字的一筆一畫中。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數學與漢字的結合,打開了漢字進入計算機的大門。
他利用輪廓加參數的數學方法將龐大的漢字信息壓縮了500倍,掃清了項目研制的最大障礙。他跳過日本和歐美流行的二、三代照排機,直接研制國外尚無商品的第四代激光照排系統。1976年9月,“七四八工程”中研制“漢字精密照排”的項目正式下達給北大,王選成為項目的核心。這是我國第一張用激光照排系統輸出的報紙樣張。這是《經濟日報》最后的一張鉛版。隨著這張版退出歷史舞臺,中國終于迎來了用計算機處理漢字并大規模應用于印刷的時代。從第一代照排機走到第四代,西方國家用了四十年,而王選僅僅用十余年就使中國從落后的鉛字排版跨入了先進的激光照排。隨著信息時代的推進,更多的人們開始關注計算機和漢字信息處理。為了方便使用鍵盤輸入漢字,一股編碼的熱潮驟然興起。1981年5月,《信息交換用漢字編碼字符集·基本集》公布,即國家標準-80。原國家語委副主任傅永和介紹:-80就是交換碼,交換碼對著機內碼,就是把眾多的支流到我這兒就匯成一個區,大家可以各搞各的碼,我有個交換碼,到這兒只要轉成我這個就能進入計算機。計算機,漢字編碼,信息化,這些詞匯是一個即將全面來臨的時代,對人們發出的清晰信號。1985年12月16日,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更名為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中國的語言文字工作邁出了新的步伐。在新時期,規范化和標準化成為語言文字工作的重要任務。對這項工作,有一位老人格外關注。據說,糾正報刊和出版物中語言文字不規范的現象已經是他長久的習慣,僅僅保存下來的這一類書信便條,就數以百計。這位老人就是胡喬木,他早年曾擔任毛澤東的秘書。早在建國初期,他就被毛澤東特派協助文字改革工作。他對語言文字他有一種情有獨鐘,他自己有很多研究,有很多思考,有自己的獨立見解。1973年,他就想到漢字要適應現代化的發展、信息化發展。
為了適應信息化的需要,同時糾正社會用字混亂的現象,1986年,經國務院批準,國家語委在對個別簡化字適當調整后,將1964年公布的《簡化字總表》重新發布。發布前,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的胡喬木態度格外審慎。原國家語委副主任陳章太回憶道:反復推敲,一邊輸著液,還輸著氧,兩個管子,一邊聽我們匯報,因為他把語言文字看成是一個人、一個社會、一個民族里面很重要的一種素質,影響到我們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在各個方面。如今,古老的漢字已經融入時代的脈搏。語言文字的規范化和標準化也被提升到了一個從未有過的高度。2000年10月3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公布,這是我國歷史上第一部關于語言文字的法律,它明確要求,在公務活動、教育教學、新聞出版、公共服務行業應當使用規范漢字。它的頒布,確立了普通話和規范漢字作為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法律地位。百余年來,為了民族昌盛和國家富強,一代代愛國知識分子在漢字改革的道路上執著探索,而古老的漢字置身于傳統與現代的漩渦,守望著命運的沉浮起落,它所承載的,不僅是一個民族的榮辱興衰,更是一個日漸強大的國家永遠不可忘記的歷史。